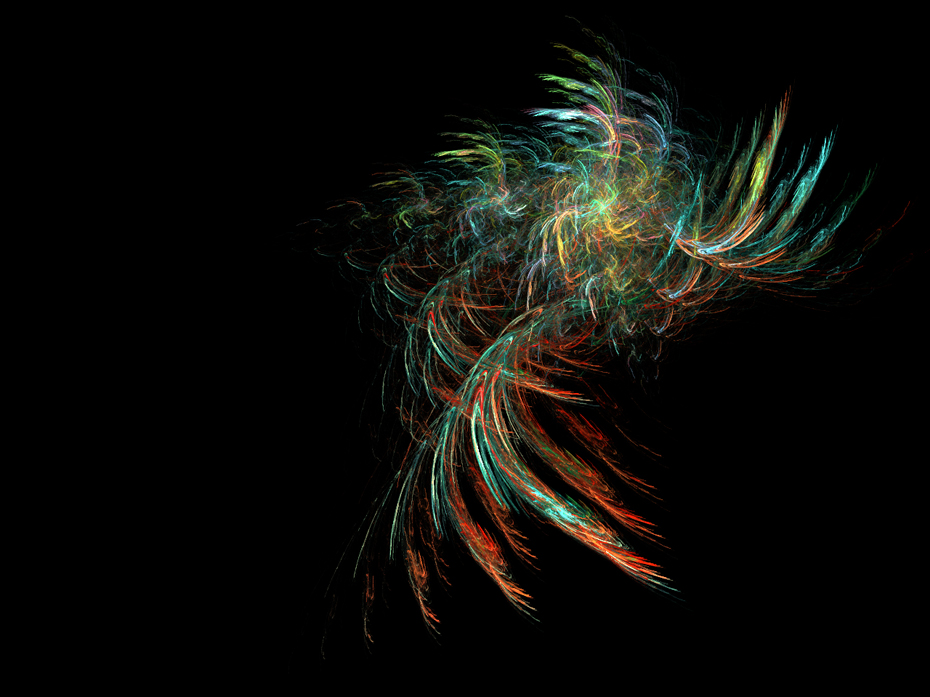事實上,任性這詞我想用在大人身上是一整個不妥當的,就感覺身體成熟了心智年齡還沒成熟一樣,有著嚴重的彼得潘症候群,好吧,是童心未泯,是赤子之心,這樣說可能就還過得去一點。
媽媽買了台相機,說是要拿來當她的玩具。實際上,這玩具可真貴,而且還是一個我沒聽過的牌子。聽說她就在別人的遊說之下衝動買下了。實際上,我媽是個完全不懂得電子產品的人,她只會按遙控器上面的電源鍵,像冷氣,她不知道功能鍵之類的可以轉換冷氣或是除濕,所以有那種日子是,打開了除濕睡覺結果一晚過後起床像水分蒸發的青娃。
今天去台藝找房子的時候,不巧的敝人的相機在遙遠的新竹,總也不能跑到新竹去拿吧。想說前天媽媽買了台相機,反正她也還沒用,那我就拿來試用看看好了。當初她買了那台相機,非常貴的玩具,被我們嫌得要死,說買這種消費性電子產品幹麻不找我們幫妳看?不過她是很固執就對了。
本想著要去跟她拿,轉念一想。這好像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她說出所謂「玩具」這個詞。實際上,在這相夫教子近三十載的歲月,玩具從來就是一個專屬於我們的詞。我該說什麼呢,一個儒家傳統的所謂「良好美德」,正是讓我母親變得連所謂玩具都沒有的這個良好美德。除了工作,還是工作。
約莫是我六歲那年,母親買了一整箱的益智玩具,也不過是聽信推銷人員說這有益於孩童智能發展,有印象的仍是她帶著我們念的那方正的圖畫書,堅實的封面打開,裡面不是故事是在數數兒,還有些積木,至今仍安放在家裡的角落,隨著母親與我遊玩的記憶。
我母親以前是作衣服的,她說以前那時候,都住工廠宿舍,每月收到的工資幾乎是全數寄回老家。那時在台北工作,只要肯作,薪水總是不會虧待的。直到後來沒作衣服了,家裡仍舊放著一台縫紉機。有時就看她幫家人改改衣服,補補破口,日子也就這樣過去。一日,母親第一次拜託我幫忙她穿個針線,那時,我仍未知覺母親已然衰老的徵兆。
有一次,看著母親踩著縫紉機工作時,聽著一聲哎呀,靠過去看,母親的手指不小心給針穿了過去,從指甲的中間汨汨的流出血來。細看,母親的指甲好粗糙,凹凸的面佈滿著灰或淡黃或褐色,那是一雙佈滿繭的雙手。我說怎辦,那時年紀也小,根本就不懂得怎麼處理這類的。母親淡淡的說,不用了,吸吮了傷口一下,看她打開了縫紉機某處的蓋子,裡面放著一層黃澄澄似油的東西,見她沾了一些,然後就繼續工作。見我還在旁邊,便說,在這看幹麻?快去做自己的事情阿。
有時候母親會拿著我的手端詳,說我的手好命,說是讀書的料子,說以後可以怎樣怎樣。我現在深知,我這雙尚未體現現實勞苦的手,正是以我母親的粗糙、長滿繭的的雙手換來的。
所以,聽著家妹說,怎麼買了台這麼貴又不實用的玩具。便告誡她別在說了,畢竟,過去總是她順著我們,依著我們。
讓她任性一次也好,幾次都好。她可以任性,她有權任性的。
畢竟,我們已經擁有太多的玩具。
而這只是她第一個玩具。
任她吧。